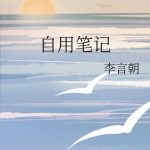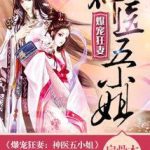《聯邦先驅報》深度專題—人物簡述:“帝國的遺産:少年軍與醜聞誕生之地”
撰稿人:安德雷·沃羅寧
01
戰争在莉莉出生前開始,在她十六歲那年結束。
莉莉在孤兒院長大,對于自己的雙親一無所知。與許多境遇相似的戰争孤兒不同的是,撫養莉莉的兒童福利設施隸屬于帝國少年軍。這些“福利院”向公衆開放收養,但身在其中的孩子深谙不成文的規矩:福利院的孩子一旦過了某個年齡段,就不再會進入可供領養的名單,而是在十二歲時收編入帝國少年軍。
少年軍是已然傾覆的帝國在國際上最為臭名昭著的機構之一,被視為這一政權有違人道的鐵證。最初海外輿論大都認為少年軍是帝國政府在漫長戰争中培養忠誠下一代狂信者的工廠,這類機構的存在确實令人擔憂,但其邪惡性質主要在于對将來的威脅。在成員踏入社會之前,他們的危險性似乎要遠遠小于神出鬼沒的帝國特工。但兩年前震驚多國的複活節使館襲擊事件證明這個推斷天真且傲慢。
4月3日,兩名帝國少年軍成員喬裝為戰争難民,前往流亡政府在B國首都的使館、假稱尋求庇護。他們在使館內引爆了身上攜帶的爆炸物。包括兩名未成年襲擊者在內,共計18人遇難。複活節使館襲擊是帝國在敵對國境內最成功的一次行動。B國的流亡僑民團體深受震動,一度人人自危。
但在此次襲擊之前,少年軍就已經不再只是灌輸帝國意識形态的教育機構。少年軍連隊逐漸包攬在前線操縱無人機和部分大型戰鬥器械的任務。這類作戰講求反應速度、和想象力,事實證明,少年軍的青少年非常适合這個新定位。
莉莉第一次上前線戰鬥時十三歲。“我們其實不在真的第一線,看不到敵人的臉。他們只是地圖上需要被除掉的紅點。戰鬥……殺人沒有實感。和模拟游戲沒有差別。”這麽說完,她停頓片刻,“當然。後來我知道那是有區別的。”但當我詢問差別具體在哪,莉莉不願意回答。不止是莉莉,我采訪過的許多前少年軍成員也對戰争最後三年的經歷諱莫如深。那段日子中有什麽是不可說的。
最後的攻防戰中少年軍對盟軍的抵抗之頑強血腥已經十分著名,不需要冗述。只從盟軍一側看待問題,很容易将少年軍成員看作被不幸洗腦、義無反顧為帝國大業抛灑熱血的活祭品。但與更多前少年軍成員接觸後,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個體體驗更為複雜。自诩自由世界的各方媒體宣揚的“洗腦”論否定了帝國時代個人意志存在的可能;而事實上,哪怕在帝政統治下,即便再有限,少年軍成員還是有選擇的空間。他們要面對的往往并非不配合就反抗這樣極端的二元選項,而是“要配合到什麽程度”“怎麽做才對自身更有利”“是否有絕對不能觸碰的底線,如果有,底線在哪”這類更複雜精細的問題。
另一方面,無可否認的是,那三年帝國上層做出的決策給許多如今最多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留下了超出語言表達極限的創傷。舊歷17年,帝國控制下的區域少年軍規模大幅度擴張。原因在于戰局劇變。反帝國聯盟于當年正式成立。盟軍首先以無人機發動精準快速打擊,毀掉帝國軍在西南方工業重鎮的所有軍工廠。帝國軍依賴的精密戰鬥設備供給鏈受到重創。兩條戰線上都出現戰力空缺。
于是,先是16歲以上,再後來14歲以上,适齡孩子都必須應征入伍。擴招前就加入少年軍連隊都升格為精英部隊。但升格的這些少年軍成員被視作“假精英”,原來的精英連隊則是“真精英”。執行複活節使館襲擊的那兩人來自少年軍中歷史最悠久的核心連隊。
“被選中執行這種任務的都是精英戰隊中的‘真精英’。”莉莉向我解釋少年軍內部的複雜等級和分支架構,甚至畫了一張簡單易懂的圖表。我與她談話的背景音是首都市中心的喧嚣雜音,在那種環境下聽一個小自己十歲的孩子對帝國那迷宮一般的體制侃侃而談,非常怪誕,又有些教我毛骨悚然。
十四歲之後,除了少年軍內部時有時無的教導,莉莉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但她能準确無誤地應用一些複雜的長詞語,做精确成熟的表達。比如:“雖然‘我們’都是少年軍,但少年軍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所以也可以說,根本沒有什麽‘我們’。”我問她是在哪裏學會“同質”和“整體”這些詞彙的,她靜靜回答,在改造營。我又問這個想法是否是她自己思考得出的結論,還是從哪裏得來的啓示。莉莉重複,在改造營。
戰争結束後,改造營是在各地血腥的保衛戰中幸存的少年軍被送往的下一站。
02
舊歷20年,帝國軍戰敗。
如何處置大批未成年的戰俘成為新聯邦要面對的一個棘手問題。改造營系統是解答。最初聯邦政府負責人們設想中的是一個“改造系統”,而非被嚴密看管起來的營地。
“我們那時想要盡可能地還原我們認知中的校園,而不是監獄。我們天真地以為只要将帝政下的暴行揭露出來,那些孩子就會意識到他們是一個巨大騙局的受害者,砰地一下,他們的思考方式會轉變,然後他們就可以回到社會,重新上學、工作。”奧爾夫·波爾金,學者、改造營項目最初的發起者之一,說到最初的構想時情緒依然激動。
帝國統治下,波爾金很少直接參與政治活動,選擇潛心于古魯爾文字的研究。但他也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曾經建議在帝國少年軍內部推廣更全面的通識教育;在新聯邦建立後,他積極與政府合作。然而波爾金構想地着重通識教育和柔性幹預的方案很快被迫中止。
和約生效小半年後,位于首都郊外的萊辛改造基地于舊歷20年11月29日開放。那裏原本是一座療養院,倉促改建為改造設施:樓面被重新分隔為教室和宿舍,來看望病人的家屬停泊車輛的停車場改為操場。另一部分原本是醫療樓的中高層成為辦公樓,但改建只進行到一半,因此那些建築物有種異常陰森的氣息。
次年2月14日,原本隸屬精英戰隊的前少年軍成員控制了基地安保系統、劫持教員,試圖發動武裝政變。“複興帝國”是那些激進成員的口號。聯邦政府不得不出動軍隊,事态在長達72小時的對峙和游擊戰後終于平息。兩名被劫為人質的基地教員喪生,交火雙方的具體傷亡數字至今沒有公開。由于少年軍和帝國軍隊都穿着黑色制服,而這起事件發生的日子又實在過于諷刺,那三天的動亂被稱為“黑色情人節”。
而莉莉那時就在萊辛。她是進入萊辛的第一批學員,在那之前,她和其他少年軍成員一起等待未知的命運。回憶起那段等待的歲月,她聳聳肩:“許多人覺得我們會全部被處決,也許那樣其實更好。”我很難判斷莉莉是在開黑色玩笑還是說真心話。
談及萊辛動蕩的72小時,“那三天感覺又回到從前。”莉莉這麽說着,流露出嘲諷的表情。她并不贊同那些無法放棄帝國幻夢的少年少女。莉莉和其他不願意加入政變的學員一起躲了起來,逃過一劫。她自稱在福利院的時候,她就對帝國思想教育不太熱衷。她是個有主見、甚至有些頑固的孩子。
“我不喜歡讓人教我該怎麽思考。但我沒有表現出來。所以我沒被槍斃。”莉莉輕描淡寫帶過的是另一些少年軍成員敘述過的高壓恐怖統治:要求絕對忠誠,故意設置多重互相監督的機構,鼓勵舉報,叛徒會被處決。這一對于少年軍的刻板印象似乎只在戰争最後幾年确實存在過。去年多地發現的亂葬崗中有大量兒童的遺骸。短短數年內,在懷疑和內耗中喪生的犧牲者數量就已然駭人聽聞。猜忌和恐懼也足以在親歷者身上留下永久的傷痕。
第二次見面時,莉莉比前一次放松,和我說了一些更具體的戰時經歷。連隊內的氣氛取決于指導員。莉莉見過毫不猶豫讓少年軍當誘餌或道具犧牲的指導員。她詳細敘述,每天會有一隊被抽簽選出來去探測無人區,有不少人就是在那樣的任務中踩中紅外控制的地雷死去。這樣令人起雞皮疙瘩的事例有很多。但莉莉也曾經被指導員舍身救下。“他對我和另外幾個做了個噤聲的手勢,然後就爬出戰壕。他跑出一段路,故意鳴槍吸引注意力。我們拼命往反方向跑,最後逃出了包圍。我們知道他那是去送死,為了我們。誰都沒說什麽。但我們都知道我們永遠會記得那晚上。”
在敘述這些經歷的時候,莉莉的聲調和表情十分平靜。在我與她的兩次對談之中,她幾乎始終維持着這種第三人敘述者般的态度,有時顯得頗為冷漠。當我問起這一點的時候,她微笑了一下,反問我:“如果我不和自己保持一點距離,我該怎麽和你說這些事?”我又問,她覺得和她一樣對于帝國灌輸的理念心存懷疑的前少年軍成員有多少,她無所謂地聳肩,幹脆答道:“我不知道。”
許多前少年軍成員對于帝國抱有強烈的憎恨,他們感到被虔誠地相信過的人和理念一同欺騙背叛。莉莉對于決定了人生軌跡的秩序似乎不抱持這種激烈的感情。“人都差不多。”她這樣的評語中隐含對于取代帝國的新世界的猜忌。
另一些時候,莉莉會自相矛盾。她否認少年軍是一個同質自洽的共同體,暗示她對于少年軍的歸屬感不強;但她也承認特定情況下,前少年軍的身份對她來說是一切。“即便我不是個模範的少年軍成員,但我确實是其中一員。我曾經感到除了那段日子,我一無所有。”
我追問那具體是什麽時候。
“在改造營待了半年之後……在我放棄畢業的念頭之後。還挺奇怪的,當少年軍不存在之後,它反而變得更加重要了。”說完這些,莉莉難得沉默了一段時間,“現在我不再那麽覺得了,但我……還有其他人都不可能假裝那沒發生過。對于很多人來說,我曾經是少年軍這件事是決定性的。我沒辦法反駁。我想相信人是可以改變的,但過去是唯一我改變不了的東西。”
莉莉确實對于人心有着超出年齡的洞察力,但因為對他人抱有強烈的不信任,很多時候顯得尖刻無情。在萊辛任教過的一位教員A(本人要求匿名)告訴我,莉莉的無動于衷和刻薄都令人印象深刻。揭露帝國軍暴行和普通人生活慘狀的紀錄片場常常哭聲一片,但據教員A所說,莉莉沒有哭過。她還會在課堂上問一些刁鑽又并非毫無根據的問題,如果教員答不上來,氣氛往往非常難堪。莉莉的意圖也許并不在于為帝國政權辯護,只是忍不住指出一些邏輯不通順的地方,但聽者不免往那個方向想。
莉莉這種态度在招來了麻煩。
在黑色情人節之後,改造項目的目的和形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通識課程基本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高強度的政治思想課程、讨論會和講座。安保措施和紀律管理也變得都極為嚴格,“基地”就此成為封閉性的“營地”,學員的自由被軍事化管理的日程和各種規章制度限制,教員開始佩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教官”。但改造系統的運營和規劃本質依舊十分原始,走一步看一步,不斷根據情況改變調整策略。
奧爾夫·波爾金回憶起離職前與繼任者交接的場景時義憤填膺:“那時候我看着來抄家一般闖進辦公室的那群人,我就覺得改造項目肯定會失敗。看看都是些什麽人!在少年軍手下吃過苦頭的地下抵抗組織成員,對帝政統治的了解停留在新聞報道層面的海歸者,盟軍指派空降的官僚……如果說我和同僚們是天真的空想家,那麽後來的這群人就完全把自己當監獄長看待。他們完全不了解少年軍內部構造,也并不把那些孩子當人。”
白發蒼蒼的學者從電子煙鬥裏吸了好幾口,才繼續對我說:“我知道有很多孩子幹了壞事……非常邪惡非常可怕的暴行,但他們也是人。大人也一樣。殘暴也是人性中的一面,所以我們需要教育,需要道德,它們是管束毒蛇的大棒和枷鎖。應該負責的是讓孩子太早成為邪惡的大人的那些家夥,而不是孩子自己。”他看向我,露出一個有些難為情的微笑:“我知道我這套思想現在已經過時了。但我還是覺得,我們真正的仇敵不能是孩子,那樣的話,這個世界真的不對勁。”
波爾金的想法在和平搖搖欲墜的戰後第一年缺乏立足之地。發生在南部港口城市D市的前少年軍成員襲警事件、第二大城市議會廣場的自爆襲擊都只令運營層的态度變得更為堅決。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出現,學員們“畢業”的要求又多了一道手續。完成課程、通過測試之後,他們還必須歷經為期一到兩個月的觀察期。便衣考察人員和電子監控網絡會嚴密監視學員,确保每個畢業的學員都真正洗心革面。
而在職教員對于輔導的少年少女們也抱有戒心,學員與教員之間爆發沖突成了家常便飯。進入萊辛半年左右,莉莉開始脫離學員嚴格的日程表安排。曠課、拒絕參加各種集體活動,破壞公物,甚至對教員動手。她的履歷上因此都是記過和禁閉記錄。她并不打算為那時自己的行為辯護:“我也把他們(教官們)當成了敵人。在那種環境下,矛盾很容易激化。‘既然你們覺得我是個激進分子,那麽我就變成那樣給你們看’,差不多是那種感覺。情緒上來的時候,我會做得很絕。”但她看起來并不後悔,好像在說,再來一次,她還是會那麽做。
由于“不守紀律”加上拒絕溝通,短時間內,莉莉接連更換了兩任指導教官。教員A是其中之一。“我們不想再經歷一次事變,所以容易反應過度,把任何質疑的聲音都當成是狂熱分子。”她對于那時候将莉莉視作帝國狂信者感到內疚:“如果我更耐心一點,也許之後的事都不會發生了。看到新聞之後,我立刻知道那是她,那糟糕透了。同為女性……不論她是不是個好學員,她都不該經歷那些。我感覺自己也是加害者之一。”
她指的是造成轟動、占據過去半個月各大媒體頭條的“萊辛醜聞”。
萊辛醜聞不僅揭露了現有改造系統醜惡的一面,更暴露了所謂觀察期形同虛設。
03
今年1月19日,萊辛改造營在任教員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墜亡。警方調查後認為斯坦藥物誤用過量産生幻覺,從其辦公室的窗口跳了下去。這個新聞在當時并沒有引發太多關注,畢竟那時所有人的焦點都在聯邦廣場的宮殿內上演的組閣政治大戲。
6月6日,帝國軍無條件投降暨停戰一周年紀念日,那也是萊辛改造營新一批學員畢業、正式告別近似戰俘的身份的日子。
當日早晨9點左右,名叫阿列克謝·馮霍恩的少年從萊辛改造營的某棟舊樓窗口一躍而下,當場死亡。
那天離阿列克謝的十八歲生日還有半個月。而他選擇的那棟樓正是四個多月前斯坦墜亡的同一建築物。在踏出無可挽回的那一步之前,阿列克謝給各大媒體發送了一段視頻訊息,那是長約五分鐘的驚人自白和告發信。他聲稱斯坦的死并非意外,而是他殺,兇手正是自己。據阿列克謝所言,斯坦長期對指導的學員實行性侵害,同時用藥物對受害者進行精神控制;受害者是阿列克謝的朋友,他在義憤下殺死了斯坦。
諷刺的是,阿列克謝原本是當日畢業典禮的學員發言代表。而在事件發生前,負責指導評估他的多位教官都對于他成功被再教育深信不疑。阿列克謝是從哪裏獲得了拍攝視頻的設備、在哪裏設置好定時發送的郵件的,目前都是未解之謎。能夠确認的是,改造項目引以為傲的觀察期跟蹤調查沒有察覺他行為中可能的異常。
半軍事半政府機關的掩飾行為,性侵未成年人,藥物濫用,司法公正,這一事件集齊了争議性的關鍵詞,迅速掀起輿論狂潮。雖然阿列克謝的視頻很快在各大信息平臺被删除,但還是不斷繼續在用戶之間流傳。這一醜聞還牽起了另一樁在首都市法院受理的未成年相關案件,3月,傑克·威爾遜被提起公訴,涉嫌傷害多名未成年人。傑克·威爾遜正是阿列克謝在視頻中提及的萊辛改造營紀律管理委員會負責人,被起訴時威爾遜已經被免除改造營職務。
6月6日當日,萊辛改造營管理層舉行新聞發布會,運營負責人辭職,管理層大換血,接手萊辛的新班底承諾徹查事件真相,并懇請媒體保護當事未成年人的隐私權。此後,改造營方面就維持沉默。6月7日,首都檢方宣布重啓對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坦死亡案的調查。截止本報發稿時分,檢方調查還在進行中。檢方在6日事件現場發現了署名收件人“警察”的塑膠袋,據悉裏面有裝有疑似藥物的顆粒的小瓶,還有另一部分證物。死者遺體已經進行過司法解剖,由于沒有前來領取的親屬已經火化。加之現場取證困難,不少司法專家認為公衆不應對調查結果抱過多期待。
而在這一切發生的數日之前,我與莉莉第一次在首都市中心某處見面。
第一次采訪期間,我與她談論了莉莉在福利院的童年和黑色情人節。兩天後,我與莉莉第二次見面。她在我對面坐下的那一刻,我感覺奇怪地不自在,仿佛有什麽将要發生。
“先生,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些事。”這是莉莉的開場白。
我和莉莉更早之前因為一個偶然在市內相遇,她那時得知我對于對數月前萊辛教官墜亡案有興趣。直到現在我都無法解釋為什麽,但第一次看到那條新聞的時候,一陣惡寒蹿上了我的右邊手臂。而當6月初的那個午後,莉莉平靜地說出下一句話時,我感覺到了命定般的惡意:
“四個多月前死去的斯坦教官是我的指導教官。”
那天的談話讓我得知了遠超我預期和想象的事。其中并不包括斯坦的死亡真相。但莉莉吐露的一切還是令我失眠了。我告訴自己,在動筆之前,必須再繼續找別的相關人士查證核實。
兩天後(也就是6月6日)早晨,我被片刻不停的消息聲驚醒。點開送到《先驅報》公共郵箱中的那段視頻之後,我感到有必要将這篇報道盡快寫出來。
04
斯坦尼斯拉夫·斯坦是莉莉的第三任指導教官。
在黑色情人節之後的改造營體系之中,指導教官與學員每周日進行面談,學員總結一周心得,教官則評估學員的“進展”。原則上,改造營方面鼓勵教官和學員建立信任關系。教員必須遵循行為準則,教員與學員任何形式的親密關系都是嚴重違規。如果有違反行為,學員可以向紀律管理委員會申訴。如果學員對教員不滿,同樣可以發起申訴并申請調換教官人選。莉莉前兩次調換教官就是走的這個流程。
但由于教官掌控學員的表現評分、決定學員是否能夠進入畢業流程,教員在學員面前事實上擁有幾近絕對的權威。一旦紀律管理委員會不受理學員的申訴,學員就等同被困在同一名教員管轄下。不合理制度的漏洞成為犯罪的溫床。
第一次見到斯坦,莉莉覺得他“還行”。那時莉莉已然被視作屢教不改的問題少女,看上去會在萊辛待到十八歲成年,那之後被送入管制更為嚴格的戰犯收容設施。但斯坦與此前的兩任教官不同,他單腿有轟炸留下的傷,內斂寡言,但對她很和氣。斯坦沒有和其他教員一樣居高臨下地訓斥教育莉莉,而是鼓勵她到辦公室聊天。莉莉承認被長久孤立後,她偶爾會渴望有個能夠心平氣和交談的對象。一次交談之後,就有了第二次和之後的更多次。
那些看起來無害的閑談中,令莉莉印象深刻的是斯坦的辦公桌上有許多紙質書。那在戰後頗為稀罕。斯坦注意到,便開始鼓勵并指導她閱讀。如果不是戰争,斯坦也許有機會進入大學教書。至少斯坦如此聲稱。
現存開放的政府檔案中幾乎沒有關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坦的資料。他的家鄉似乎在南方,但在醜聞曝光之後,即便将南方翻了個遍,媒體同僚們也沒能找到斯坦這個人真的存在過的證據。帝國吞并南方諸多政權的戰役是帝政初期最血腥的一筆,那時不計其數的南方居民逃亡北上,南方政府投降前,內部主張抵抗到底的鷹派摧毀了基礎設施,個人信息和資料随之遺失泰半。斯坦似乎還有個相依為命的姐姐,但她在帝國軍入侵時遭到侵犯,發現懷孕後自盡。但這也是無法查證的說法。
莉莉逐漸對斯坦放下心防。她考慮過重新回去修滿課程、好好考試畢業。但信賴招來的是噩夢。“他恨帝國的一切,以它對待他姐姐的方式對待我、懲罰我,以此複仇。”描述斯坦所作所為的時候,莉莉的聲音裏出現了一個空洞。她會突然跳回時間更深處,敘述戰時少年軍內的體驗。那些經歷有共通之處。但莉莉大體上還是表現得很平靜,這讓她直白冷靜的敘述獲得了一種野蠻的暴力。
作為聽衆的我不止一次因為自己的生理性別而感到不适。我無法解釋為什麽同為男性的另一些人能夠做出如此惡行,并為我無法給出一個解釋而羞愧。想要在這篇報道中找到一些駭人聽聞的細節的讀者會失望,我會将它們留給法庭。
莉莉試過申訴,但傑克·威爾遜與斯坦有交情,她的控訴石沉大海。由于她的“惡名”,雖然她的精神狀況肉眼可見地惡化,教員和其他學員理所當然地認為那只是頑固分子的瘋狂。莉莉在那段時間更加頻繁地“違反紀律”,故意違反每一條可能違反的規矩。少年軍的身份變得重要。她開始自殘,試圖輕生。學員身上的生理數據探測裝置讓她一次次被從死亡邊緣拉回來。她有嚴重的睡眠障礙,但因為她會将安眠藥囤積起來,醫務室最後拒絕給她開藥。
“所有人都看得見我,但我也是透明的。有時候我感覺自己是一個污漬,他們都恨不得我快點消失,但又不願意給我自願消失的權力。”
我很想寫,莉莉并非完全孤身一人。但那種說法淡化了她經歷的孤立和漠視。在我們的對話中,我小心地詢問有沒有哪怕一個人注意到她的狀況,莉莉以陳述事實的口氣告訴我:“我試過告訴自己我是愛他的。但最後,我實在做不到。如果沒有阿廖沙,我早就死了。”
阿廖沙是阿列克謝·馮霍恩在萊辛改造營內更廣為人知的通行名字。他們是彼此唯一的朋友。與一些揣測截然相反,他們并沒有戀愛關系。莉莉堅稱他們的關系連朋友都夠不上。采訪中,她花了很長時間試圖給與阿廖沙的牽絆定性,不是朋友,不是戀人,甚至不是同類。莉莉說她也不了解阿廖沙,有時候甚至會怕他。到最後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了他們的關系。無疑的是,他們對彼此有特殊的意義,極度依賴對方。“我會為他做任何事,他也一樣。”這句話在如今看來,更像噩兆。
6月6日之後,我試圖追蹤阿列克謝的生平,但很快走進死路。能弄清的只有他被赫伯特·馮霍恩——一位前帝國外交官——收養,因此獲得了這個姓氏。關于馮霍恩一家有許多傳言,但無一能夠确鑿證實。帝國投降之日,馮霍恩一家在家中地下室服毒自盡,所有私人和官方機密文件都被事先付之一炬。馮霍恩家的養子不止有阿列克謝一人,我在一所醫院找到了幸存的唯一另外一人。他在被征入少年軍後負傷,雙目因激光照射失明。但他拒絕談起在馮霍恩家時的任何事,對于阿列克謝,他只說“無可奉告”。
而莉莉的敘述也在1月19日那裏突兀地中斷了。她開始模棱兩可,不再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只說斯坦需要服用很多止痛藥來蓋過腿部舊傷,有時候也會依靠名為“愉悅”的藥劑提神。他服藥過度并不讓她驚訝。随後,她就跳到了斯坦死後。
采訪時我就認為她顯然知道什麽,但她還不夠信任我。
莉莉沒有提及阿列克謝對斯坦的态度。她對于斯坦之死異常的沉默是否是對阿列克謝的保護?我詢問她為什麽要接受采訪,告訴我她告訴我的一切,她是否想要正義的裁決。莉莉笑了:“我要正義有什麽用?我想要更多人知道這些。也許在另一個營地有另一個我。說不定還來得及。”
但莉莉可能也沒料到更多人會以那樣的方式知曉這一切、比她願意對我透露得還要多。
事件發生之後,莉莉由于情緒失控被送醫。
05
萊辛醜聞曝光之後,莉莉短暫進入過公衆視野一次。
三天前,莉莉受檢察官傳喚,為重啓的調查作證。檢察院門前全都是事先得到消息的媒體。下車到登上臺階進入大門內的這段路兇險、易于發生沖突和意外。她戴着帽子和口罩,在改造營和檢方人員的陪同下前行。檢察院方面準備不足,場面非常混亂。
有人搬出從萊辛畢業的前學員的說法,詢問莉莉是否與斯坦有戀愛關系,他們的糾紛其實是男女糾葛引發的情殺,她是否真的在案件當日神志不清。甚至有記者質疑阿列克謝·馮霍恩自白的真實性,暗示他和莉莉只是以極端的方式博取公衆注意力,意在美化少年軍形象。不知道是誰喊了一句,如果她真的有勇氣證明改造系統的弊病,那麽應該真的站出來,而不是那麽蒙頭捂臉地藏住身份。
莉莉站住,突然将帽子一扔,然後去扯口罩。在場所有人都看到了她怒氣沖沖的眼睛。
“那好,給你們看就是了。反正我沒有什麽要藏的!”那時的莉莉是平靜的所有反義詞,和與我談話時判若兩人。
同行的人立刻用身體遮蔽住莉莉,但還是有記者抓拍到了口罩落下的瞬間。
場面失控,莉莉被立刻送回車裏。同行的改造營教員與拍照的記者爆發口角,險些升級為肢體沖突。最後,在現場的一位備受尊敬的資深同行走過去,将相機搶過遞給那位教員:“我們還不至于不像樣到這個地步。”
那天的沖突成了記者圈子裏人人見面都要議論幾句的話題。
莉莉同意接受采訪的時候,預見到了自己可能會面對的攻擊,并且對此直言不諱。在采訪中,她有兩副聲音,一副聲音用詞直接到粗俗,另一副圓滑而老練。
“大概會有人叫我叛徒,不論是帝國還是這個新秩序,我對哪邊都沒什麽感情。我不覺得改造制度本身應該被廢除。有人的确被它幫助甚至拯救了。我還有其他少年軍成員從小理所當然接受的許多事确實是錯誤的,必須有人告訴我們。但方式出了問題。”
“大概還會有人罵我是狗雜種是婊子,但那和我沒有關系,我不在乎。”說這話的時候,莉莉露出了鬥士般的無畏神情。
停頓了一下,她露出真假難辨的諷刺表情:“但我也不知道有什麽辦法。只是把另一個版本的正确事實塞進腦子裏沒法真的讓人改變想法。而如果要打感情牌,就會一不小心走得太近,那又會成為新問題。不管怎麽說,也許我這代人的一部分人就是無可救藥。我們是帝國留下的一筆難處理的遺産,不能扔掉,但是放着也只會造成麻煩。等我們被淘汰幹淨,問題就解決了自己。”不等我說話,她又笑了:“不過,‘我們’到底是誰呢?”
06
采訪倒數第二個問題,我照例詢問莉莉對于未來的計劃。她像是早就準備好應對這種問題的答案,應得有些太快,但又十分有她的風格:“我不知道,先生。如果不介意的話,你能不能給我一點建議?”但明擺着她不需要也不會接受他人的建議。那态度讓觀者不免有些擔心她是否會因為過于有主見而做出無法挽回的決定。但我不覺得自己有資格對她說教。她的人生經驗遠遠要比我複雜沉重。
最後,我告訴她,依照法律,我撰寫任何相關稿件都必須使用化名。我想知道她是否有偏好或是忌諱。她